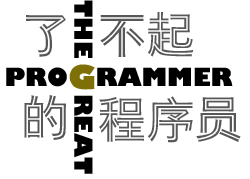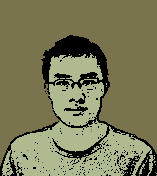浅析普通话声母X在邵阳方言中的读音
2013-07-16
年初在家的时候,电视上在放一档名为“寻情记”的节目,老妈路过,无意念了一声节目的名称:秦琴记。没错,寻字读成了秦【1】。在家乡话里,要表达找东西的意思时,的确是说“秦”东西,但对我这种打小就学习普通话的年轻人来说,照着字文读,则只会读作“标准”的“寻”。母亲这句随口说出的话,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此外,普通话声母为X的字,在方言里常见的异读可以是H,可以是S,怎么会读作Q呢?自家姓谢,老式的家乡话甚至把作为姓氏的“谢”读作“Jie”,这又是为什么呢?有些常用字,如“下”,家乡话读作零声母“ia”,这就更有意思了。
记得当时在人人网上,一位杭州的同学也关注了这个问题,他罗列了一些杭州话中X声母的有趣发音现象,并作了一些解释。从他的解释来看,这位同学对于音韵学并没有太多的了解,在这种情况下,能够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发现问题,真是很有眼力。在大半年之后,自己也学习了一些音韵学的边角料知识,打算针对自己的方言,对这个问题做个解答。
普通话声母X在邵阳方言中的读音,大概有这么几种:X、S(Si或Sy,即后跟撮口音)、H(如“限”、“衔”等)、(零声母)、Q(如“徐”、“祥”等)、J。其中Q和J也许可以归为一类,差别只在送气与不送气,而本乡发音很浊,它们的来源或许差不多。S音在其他方言中很常见,在邵阳话中极少出现。
现在普通话声母为X的字,在普通话方案确定之前,在北京话、官话里分为团音和尖音两种读音:X和S,前者如“向”,后者如“心”,现在的吴语、粤语、闽南语等南方方言及很多北方方言依然读作“sin”。大概在明清年代,我的家乡话中很多尖音已经读作团音了,所以现在家乡话里“心”的读法和普通话一致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在翻阅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X项下的全部词条时,发现“旬”(尖音,syun)这个字,老式的发音确实是尖音。类似的情况还有个常用字:俊,记得小时候我们为了模仿老人们的奇怪发音,如果有同学名字中有这个字,或者形容一个人长得漂亮时,就会故意发作老式的发音,读作“zyun”。这些都是尖音在老家方言里面的遗迹。
而汉语原来读作团音X的字,其中不少在一千多年前读作H。一千年看起来很遥远的样子,但这些字在现代方言里保存很多,用大家都有所了解的粤语举例,如“喜欢”的“喜”(粤语大概读作hei)。这类字在邵阳话中也是比比皆是。H和X一个用舌根部发音,一个用舌前部发音,H转变成X,可以说是语音发展的一个规律。事实上,普通话的H对应的国际音标就是X。如果读者是足球球迷,那很可能注意到了西班牙球星哈维的名字写的是Xavi,据通晓西语的球迷介绍,似乎既可读作Ha,也可读作Xia(更准的也许是Shia,但普通话怎么标都有差异),个中的道理大概类似吧。
另外再举一例:学。现在即使在方言里,说起“学校”、“学生”、“学习”这些词,“学”都发成普通话的音,但是在一些固定词语中,比如表示模仿时,本乡方言用的字是“huo”,这个字我们打小就用,但我一直不知道对应的汉字是什么。去年看昆曲《水浒记·借茶》,中间的男主角张文远老是称自己为学生,张文远的念白用的是中州韵,听起来就像是“和尚”,这么听了几次,才恍然大悟,原来“huo”字就是“学”呀!此外,“孝顺”的“孝”,如今只有在固定词语“孝衣”中读作“hao”了。
如果稍微留意一下本乡方言中将普通话声母为X的字读成声母为零声母的字,如“下”、“熊”、“嫌”等(女孩们喜欢说的“讨嫌”,以前我都以为是“讨厌”,但声调又不同,一直疑惑至今),可发现它们的共同点:声母都属于古匣母字。所谓匣母字,意思是在古代和“匣”这个字同声母【2】。在著名的《广韵》(写唐诗什么的,是否押韵的标准工具书)中,属于匣母字的反切上字(反切注音法中表示声母的那个字)中,有这么一些:胡、户、下、侯、乎、何、黄、护、怀;于、王、雨、为、羽、云、永、有、云、筠、远、韦、洧、荣(分号前后的字有区别,但都可以列在匣母下)。
在这么一大串字中,根据它们现在的读音,可以大概了解匣母字的演变。在这里,可以提一下“黄”和“王”这两个字。这二字,现在普通话中声母已经不同,但是在邵阳方言以及很多方言中,它们的读音还是相同的。不过据说——据不知名的非专家说——老式的吴语,“黄”和“王”是有微弱区别的,果真如此,就有意思了。
下面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:“下”和“吓”。这两个字长得很像,在普通话中读音也相同,但在本乡方言中,“下”读“ia”,“吓”读“ha”。查《广韵》可知,“下”的反切是“胡雅”,“胡”字属匣母,“吓”字的反切是“呼讶”,“呼”字属晓母,它们确实有所区别。这种冥冥之中暗含的规律,也许就是语言的迷人之处吧。
最后,就是最异常的发音为Q和J的一类字了。对此,我最初的猜想是,它们可能都是尖音字,由于本乡发音偏浊,S读成Z,尖音变团音后,跟着演化成Q和J。这样的解释不堪一击,因为这类字尖音和团音都有。不过在最后,在老老实实拿出字典挨个翻看X的条目时,才发现答案如此明了:在《广韵》中,它们的反切上字都属于邪母。比如说,“谢”字的反切是“辞叶”,“辞”属于邪母,“详”、“寻”字的反切上字是“徐”,“徐”属邪母。
这里同样举出一个有意思的例子:相像。普通话里是个双声叠韵词组,很有韵律,但在本乡方言中,虽叠韵但不是双声,“相”依旧读作“xiang”,“像”却读作“qiang”。在最初猜想尖团音的原因时,就想到这个词,而“相”、“像”都是尖音(这个词要苏州同学来读,就是“siang z(s?)iang”了,很好听),俨然一个反例。
老实说,我没有把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每个声母为X的字都考证过,其中一些字属于书面用语,方言里没有,一些是因为偷懒,不想去查了,大概的情况见附录。我对这种有渊源的东西有着深厚的兴趣,类似的有足球战术发展图谱:据英格兰的懂球帝Jonathan Wilson考据,阿根廷那一类的南美足球风格源自中欧,而中欧的足球风格来源一个在英格兰无人赏识的战术大师,至今在南美,还有一个类似哥伦布的角色的足球人时常被提起,就是他把传控足球的理念从中欧带到了南美。
【1】 确切的说,不完全是普通话发音的“秦”,而是一种介于Jin和Qin之间的发音,声母为送气浊音,而“琴”字和普通话一致,声母为送气清音。普通话只有不送气浊音(J)和送气清音(Q)。
【2】 这些学术作品存留下来的全在敦煌,敦煌被掳后到如今,只能在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看到原本了。
附录(关于本乡方言的入声字,有必要说一说。本来的说法,入声字在湘方言中已经大抵没有了,好在音韵学大家、同乡唐作藩先生的一句,在长沙方言中入声字转变为一类特殊的发音,才发现不仅是长沙话,本乡话也如是。这解决了我长久以来对于家乡话中那类怎么说怎么别扭的字的疑惑,原来它们都是入声字。这类字在市区里面的发音很低沉,有个降调的过程,在我住的地方,发音为调值很高的阴平,而且很急促,但没有入声字标志性的韵尾。在附录里暂且这么记录吧):
(每个发音下的1、2、3、4代表普通话的四声,没标注的表明和普通话发音相同,附录还有一些我对个别字词的看法)
-xi 1: 西、吸(有误读为ji)、希、析、息、惜 2: 习、席、媳(都是入声读成类似调值很高的阴平,短促但没有韵尾) 3: 洗、喜 4:戏、细 -xia 1:呷(本乡文人总以此字代替“吃”,愚以为“吃”和“呷”不同,本乡所发“chia”的音,如果不是“吃”,也不会是“呷”)、虾、瞎(都是h) 2:匣、狭、霞、峡(前2个为h声母,韵都是入声读成去声,短促但没有韵尾,霞字声母为零声母) 3: 4:下(ha,ia都有)、吓(ha)、夏(ia)(!下和夏广韵反切上字都为胡,属于匣母,吓的反切上字为呼,为晓母) -xian 1:先、仙、鲜(有时读作xuan) 2:闲、贤、咸、衔(这些都是han)、嫌(ian、广韵反切上字为户,属匣母)、弦(有时读作xuan,恐玄字误读,也可能是古音一直保留至今,毕竟从字面就能看出是跟玄同声的) 3:显、险、藓(xuan) 4:县(iyuan)、现(ian)、限(han)、线 -xiang 1:乡、相、香 2:详(qiang)、降(iang) 3:享、响、想 4:向、项(上切胡!大家误读成hang了,应为iang)、巷(hang)、像(表示相像时,或读qiang) -xiao 1:肖、消、削 2:淆(iao) 3:小、晓 4:孝、校、笑、效(iao) -xie 1:歇 2:协(入声?)、斜(qia)、邪(qie)、鞋(hai) 3:写 4:泻、谢(jie,比q浊,但如杰,又读成入声qie) -xin 1:心、辛、新 2: 3: 4:信 -xing 1:兴、星、腥 2:刑(in)、行(hen,in,匣母的两种变化,在粤语读成hang)、形(in)、型(in) 3:醒 4:幸(in)、性、姓 -xiong 1:凶、兄 2:雄(iong)、熊(iong),这2个字,广韵的反切上字都是胡,属匣母 3: 4: -xiu 1:休、修、羞 2: 3:朽 4:秀、袖、绣、锈、嗅 -xu 1:虚、需 2:徐(qu) 3:许 4: -xuan 1:宣 2:悬(iuan)、旋(iuan) 3:选、癣 4: -xue 1:削、靴 2:穴、学(在固定词组中读huo) 3:雪(入声,高音阴平) 4:血(同雪) -xun 1:熏 2:旬(老式读尖音,syun)、寻(qin) 3: 4:训
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